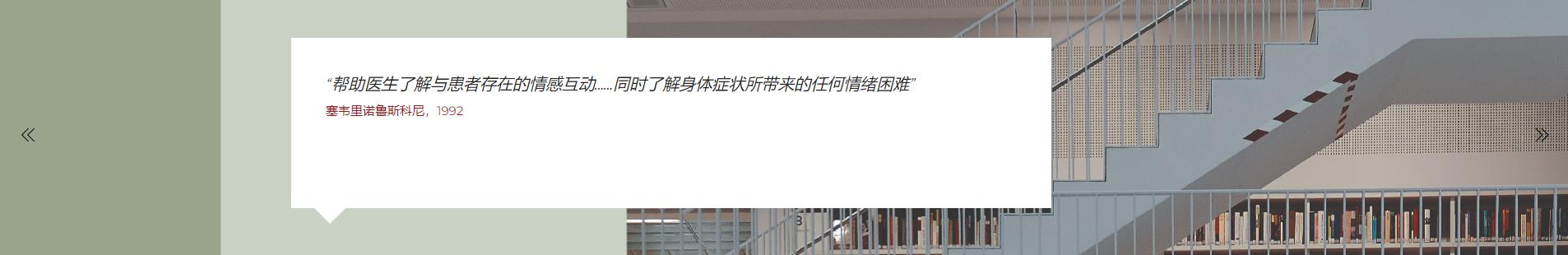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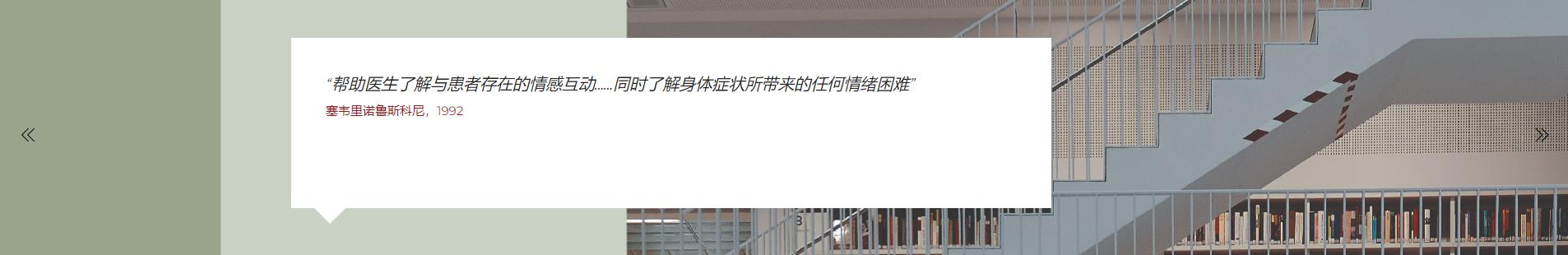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作者:Imke A. Fiedler
译者:李微笑
选自《舞动治疗督导》一书的第9章(第118-136页)
导言
本文将介绍一个舞动治疗督导的方式,这一方式源于巴林特(1957)督导小组的进行精神分析的结构。这一方式又发展了巴林特的理念;作为督导舞动治疗师的方法和过程,它改变了传统的言语情境,结合动觉和动作层面。
本文首先将简短回顾在德国的督导工作,然后将列举两个案例,以阐释作者在督导上的理论观点。本文所倡导的舞动治疗团体督导的模式可概括为7步,其中整合了动觉共情、真实动作和心身反移情。这些恰是舞动治疗的有效工具,对督导过程也大有裨益。巴林特团体的基本概念作为源头也将被提及。除此之外,移情与反移情的概念的呈现是为了强调“镜像现象”,这是精神分析取向的督导的核心概念。最后,本文还将谈及在督导中进行多分项工作的必要性。其理论假定是舞动治疗师需要思考的不仅是精神分析角度的病人-治疗师关系,还有其在小组中的专业角色。除此之外,还要理解体制结构,以更能从督导过程中受益。
背景
在德国,督导源于三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大约在1920年左右,“柏林精神分析学院”开始为其学员提供对照分析(Puehl, 1990)。受训的精神分析师同有经验的临床精神分析师探讨他们的案例,以获得专业的反馈。这一形式的督导仍存于许多治疗培训学校中,被称为对照分析(control analysis),是督导的重要根基之一。
另一根基(及其称谓)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受雇代理人”被安置于大型社会福利机构的团体和小组中进行行政、教育督导。这种形式的督导的行政意味更浓,注重对社会工作的执业者的教学、监察和控制。德国人改变了这种形式。外部的临床督导师受雇进行团体督导时,弱化行政色彩,更注重案例、个体的专业角色、和团体互动。
第三个取向则发展自迈克·巴林特,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一位精神分析师。他在团体中的案例工作尤其强调“医生-病人关系”。这一方式影响了全世界众多的执业者、精神分析师、心理治疗师、社工,及其他健康行业的专业人士。
在德国,督导的各种不同的设置和取向都发展自这些基本观点。从设置的角度看,有个体督导、团体及小组督导,还有机构督导。不同的督导取向则与心理治疗的不同流派及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相呼应:比如,精神分析取向的督导(Oberhoff and Beumer, 2001),团体动力取向的督导(Foulkes, 1974),系统取向的督导(Brandau, 1991)。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理论取向,就有多少对督导的定义(Lippenmeier, 1984; Fatzer and Eck, 1990; Puehl, 1990; Schreyoegg, 1991; Pallasch et al., 1992)。本文的督导指的是通过自我反思过程来提高专业能力的临床督导。
Rappe-Giesecke(2003)的整合取向探讨了触及不同“分项”的必要性,这是督导过程的需要。她区分出督导过程的不同分项:案例工作,角色探索,体会和沉淀自我体验,和体制分析。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谈到不同的分项有利于支持被督导者更深更广地理解自身的专业情境。
对德国舞动治疗师的督导由经“德国舞动治疗师协会(BTD:Berufsverband der TanztherapeutInnen Deutscland)”认证的舞动治疗培训师提供。协会的督导师认证标准则在2005年出台。
以下提供两个案例,或可形成舞动治疗师进行团体督导的整体印象。
案例
这里选取的案例来自于我带领的一个督导小组。这个小组由五位有经验的舞动治疗师组成,在两年中每三周督导一次。我会标记某些督导阶段,并会在后文中列出这些阶段。一些特定的术语如“镜像现象”、“一致反移情和互补反移情”也会晚一点在后文中进行定义。
我总是鼓励被督导者在督导中呈报与一个新的来访者进行的首次访谈的情况,因为一般而言,在首次晤谈中,一切都已呈现,却又不甚清晰。
案例1
Eileen,是一个私人执业的心理治疗师,也是一名舞动治疗师,在小组中呈报了如下首次晤谈。
l 言语呈报案例:Connie,一个34岁的自由职业的图形设计师,寻求个人治疗,因为数周来,她感觉到乏力、疲惫、抑郁和难以入睡。除此之外,她还描述了与其女性同事在工作中的紧急冲突。她提到她和她的同事进行了十次教练咨询,以澄清工作关系。同样,她们也从一个财务分析师那里寻求了与她们生意上的事情相关的6次的专业帮助。
治疗师Eileen提到,她觉得困惑,当听到这么多“助人者”的时候。她的印象是,这些支持体系实际上分散了来访者的注意力,并且可能让Connie很难真正地投入到治疗关系中。于是,她邀请来访者进行一个简短的动作序列来表达其目前的状况。
l 具象化:在督导小组中,我让Eileen展示她所记得的Connie的动作。Eileen用右和左臂进行了水平维度上的两侧和交叉动作,前内驱力呈现为突然和温和(小心翼翼),在中等的动觉范围中。在动作启动时多为束缚流动,动作连续中为中性流动(偏木僵状),并以手臂的死力结束动作,手垂下来。
l 言语呈报案例:Eileen描述到她试着聚焦到不同的议题上(职业上的关系、财务问题和女人的抑郁状态)。她感到了如此多的紧张感和压力,觉得来访者应该首先处理具体的工作中的冲突,应该继续完成教练和财务督导。只有在这些结束之后,再开始个人治疗。在提出这个建议后,她描述到,来访者坚持希望现在马上进行个人治疗。Eileen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助人者”太多交错在一起。Connie仍然坚持。她们最后同意两周后开始治疗。就在这一晤谈快结束时,来访者说,可能你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我会在另两个咨询结束时给你打电话。Eileen同意,Connie离开。这个结束部分让Eileen十分困惑,询问如果理解这个动力结构。
l 自由联想:小组马上开始了对Eileen推迟治疗的开始与放弃开始治疗的“对与错”的讨论。对我来说,这就像是治疗情境中的挣扎的再现。当我分析我们对治疗互动的讨论,我们意识到这是“镜像现象”。我决定从动作的层面进行这一联想阶段。两个小组成员重复了Connie的水平维度的动作,开始降低张力和速度。当她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动作变得更柔和,呈现出缓慢、间接和轻柔的内驱力。
她们表明特别需要支持,在强化动作序列结束部分的死力时感到了深深的悲伤。她们不断地在更多或更少一点束缚流中切换,她们探索着这样的束缚流是如何阻断了内在的需求以及如何帮助保持控制。
l 提问与澄清:这一简短的动作序列使小组可能接触到来访者的阻抗,感知到其对需求的阻断,和抑郁。在我们的讨论中,另一些在场的小组成员和我感知到了口欲期的被看见、被保持、和被容纳的需求。此时,Eileen认识到在那次晤谈中,她完全没有去镜像这一动作序列,而只是在合理化,在试图“理解”这些动作,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地去共情。
晤谈的结束部分看上去似乎是Connie的重大胜利,因为她以己的绝望和困苦说服了治疗师(母亲),但最终放弃,而跟随治疗师的建议成为了一个“好的来访者”。
l 反移情分析:Eileen的反应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反移情反应。小组则努力地去全面理解来访者的压抑的需求。我的内在则开始探索个中的心智聚焦点,以及Eileen角色中的情感共情的缺失。一个严格的母亲给出“好”建议的意象浮现出来。我所想到的一个解释是Eileen的心智态度可说代表了一个补充性的反移情反应。我们假定,来访者可能曾无法在情感上依赖自己的妈妈,因妈妈更多地是给出建议而不是情感上的支持。
l 建议与结论:这一案例督导快结束时,我没有给出建议,而是邀请Eileen自己用动作去探索用何种内在态度与Connie开始治疗。她坐在地板上,闭上眼睛,开始关注自己的呼吸。然后她开始在水平平面上以展开和收拢的方式塑造自己的身体。她沉静而稳定。她说,“如果我就在当下,感知和倾听我的身体,事情就会变得清晰”。
案例2
Kathryn,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舞动治疗师,来访者Mary是一位28岁的诊断为多重人格障碍的女士。
l 言语呈报案例:Kathryn与来访者已经晤谈了八周,她呈报案例的介绍性评论是,“我觉得我在泥潭里钓鱼”。她说来访者是一个功能良好的律师,长期接受个人治疗。来访者Mary提到关系上的问题,比如亲密与疏远,不信任和与女性朋友的力量挣扎。Kathryn进行了多种干预,如身体感知,立定扎根(grounding),重量感知,个人空间探索等。案例呈报的大部分内容是她的干预,以及对于治疗过程应该聚焦何处的不安全感。她指出,她不愿与来访者纠缠在多重人格障碍的心理动力议题上,首要的是去稳定住来访者,并确保动作过程清楚明显地是在“此时此地”的。
l 具象化:当我邀请Kathryn展示给我们Mary的动作印象时,她起身,笔直地站立,呈中性流。她展示出这个来访者是相当积极主动,有能力进行动作探索和简单的即兴创编。我观察到了上下半身的分裂,也常常紧锁膝盖。闭上眼睛时的动作显得可怕,互动干预也是如此,让人觉得不舒服。另外,即使在她展示后,我注意到自己也感到一片空白(直到此时仍然很难给出精确的动作描述)。
l 自由联想:小组成员自由联想阶段也相当地积极主动。她们给予Kathryn许多反馈,如她的干预如何看上去是合适的,她的聚焦与稳定和“此时此地”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几乎成为了对Kathryn的工作方式的认同会。我意识到,至此我对来访者的情况还一无所知,没有关于Mary的形象、联想,除了一点,那就是我也觉得正在“泥潭里钓鱼”。我越来越感觉到没有让小组与自身感受相关联的内在空间。
l 提问与澄清:我提到至此对这个来访者没什么感觉。我问,在案例呈报中,是否有什么东西被遗漏了。Kathryn有些吃惊,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告诉了我们来访者的童年早期的创伤。她曾经长期遭受父亲和两个兄弟的性侵害,甚至还涉及到一些道具、甚至是动物,这可说是最残忍、最恶劣的侵害了。Kathryn很困难地才能找到一些描述那些恐怖情形的语词,我们也对这些信息难以接受。
l 自由联想:片刻共鸣后,小组开始对“泥潭”这个词产生联想:浑浊、肮脏、污秽、昏暗。组内充盈着各种情绪:绝望、气愤。愤怒被释放出来,Kathryn也愈加放松。她不再需要独自容纳整个“泥潭”。也更容易看出多重性格障碍是应对早期创伤的防御。
l 反移情分析:Kathryn和小组卡在了相似反移情反应中,认同了来访者的阻抗。在分析中,这种反移情反应更显明显:来访者必须压抑创伤性的体验,她需要Kathryn站在自己这一边。Kathryn潜意识里贡献出自己去承载这个创伤,于是无法体察、充分理解这一动力。
l 建议和结论:最后我们再次鼓励和安抚Kathryn,聚焦于强化和稳定是合理的。除此之外,我强调了将创伤的信息意识化的重要性,可以在晤谈中呈现。
结束这一督导时,我让Kathryn进行一个动作序列,邀请其他小组成员为这些素材想象并创造出一个动作的容器。在这个容器中,这些素材是安全、可以接近的。
这两个案例都表明加入动作序列后所发生的过渡和改变是多么的重要。比起纯粹言语干预,舞动治疗师去触及心身潜意识会更容易一些。尤其,最后的动作序列给了被督导人从身体层面体会、处理反移情反应的机会,更有可能减少困惑和混乱。
一种舞动治疗督导的方式
作者认为,对舞动治疗师的督导可应用巴林特模式,在小组中进行个案工作。这种督导是以来访者为中心,并聚焦于来访者-治疗师的关系的。
迈克•巴林特有志与在身心医学中建立统整的取向。因为他认为培训全科医生需要提升他们对“医患关系”的理解,以及深化对心理治疗的理解。他发展出的“训练-研究小组”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医生,病人和疾病》一书中。这是第一本关于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书籍。全科医生们被邀请呈现“疑难案例”,与小组成员讨论,以获得对医患关系的更深理解。此后,这种案例讨论小组的形式被用于社工、教师和其他健康行业的专业人士。
在此,这一基于巴林特模式的督导方式也被用于改善舞动治疗师的专业技能和胜任力。这一督导方式需要对专业角色和行为的自我体验和处理保持开放,也需要对自己的治疗定位保持思考。督导的整个过程需要是非评价、建设性的。小组应该支持每一个成员,为职业成长形成一个安全的容器;也应提供丰富的创造性的资源。
这一舞动治疗督导方法分为7步:
1. 提出案例及选择
2. 言语呈报案例
3. 具象化(具身化)
4. 自由联想
5. 提问和澄清
6. 反移情分析
7. 建议和结论
1. 提出案例及选择
在实际的个案工作开始之前,小组成员提议、讨论、并决定对哪些案例进行工作。在这一阶段,许多团体动力的层面开始出现。有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提出案例(可能小组中对展现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方式有阻抗—这表达了小组中的缺乏信任)。有时,两个、甚至更多的成员相呈报案例,于是进入了争夺关系(表达出小组中的果敢与竞争性)。做决定过程的动力一方面与团队进程,与每个小组成员所处的阶段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已经与此后将处理的案例产生关联了,可被看成是前意识显现了此后在个案中会呈现的动力结构。
2. 言语呈报案例
案例呈报人被邀请谈论她的疑问和问题,在来访者-治疗师关系方面,但不用呈报笔录或任何治疗记录。记录一般已经包含了对治疗情境的二次过程的处理和思考,可以被看成是案例呈报的心智准备,却也减少了自发言语表达上的自由度,抑制了有效的反应(Balint, 1996,p.19)。治疗师本人对来访者的感受和情绪反应是最重要的。另外的一些团队成员被邀请在案例呈报过程中自由地调整注意力。重要的,不是去聚焦任何细节,而是在言辞一一呈现的过程中允许产生意象、动觉反应。案例呈报人可能在一开始会谈到她的具体疑问和期待被督导的焦点。
此时,个案信息是否完整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被督导人是如何呈报这一个案的(如,呈报一个抑郁症的个案时,有可能显得犹豫、声音死气沉沉,较少肌肉张力流)。遗漏和不完整的地方也是珍贵的,可能会提供有关心理动力方面的信息。
3. 具象化(具身化)
之后,案例呈报人被邀请用身体动作再现来访者。这并不是角色扮演,或在身体层面上假装成为了来访者,而是舞动治疗师表达自己如何内化了来访者的过程。治疗师用肢体动作、身体姿势、来访者的动作反应来示范,以在督导情境中形成对那个来访者的临在,与身体层面的印象。由此会给小组提供关于阻抗、移情反移情等方面的额外的信息,比如,Connie在水平维度上的两侧和交叉动作,又如Eileen的上、下半身动作的分裂。
动觉意识为小组成员提供了另一些感知角度。在晤谈中,动觉共情结合了身体的感知和调频共振。这一过程为更多的前意识表达与重现、初次过程、以及为所感意义的接收与言语化打开了一扇窗(Fiedler, 1988, p.30)。在此,案例呈报人再一次呈现了她的来访者-治疗师关系的方方面面,为小组成员进行自由练习过程提供了视觉和知觉材料。在见证的过程中,她们被邀请允许身体与各种动觉素材的共鸣。
4. 自由联想
这时,案例呈报人可放松,跟随小组的讨论、反应和观点。在实际的督导过程中,第4,、5、6步时常交错混合(自由联想,提问,和反移情分析)。但是,为了描述与概念化的清晰度,会在这里分别列出和阐明。
进行自由联想的能力十分重要。此时,并不要求小组中的任何人去完全理解案例,而是去添加上他们自己的反应。弗洛伊德曾说在对待注意力的态度上,自由联想与思考完全不同,因为自由联想摒除思考(Freud, 1922, p.109)。小组成员被邀请,允许出现并勇于表达各种主观的反应:好玩的,批判的,恶心的,无聊的,困惑的或愚蠢的。很多时候,那些让人感觉完全的废话的反应却是有价值的。它们被看成是潜意识的表征,或对该案例、该咨访关系、部分的来访者病态的客体关系的象征性表达。
在督导过程中,小组成员能连续地体验到移情与反移情,感知到该种动力的质感,倾听内在,而不是试图马上理解。小组成员说出他们的反应,并在所呈报的材料的基础上具体说明自己的各种官能和感知。同时,成员也被邀请去捕捉一些动作,去进行真实动作来深化动作体验(在Eileen的案例中,成员们探索水平维度上的手臂动作)。动作者和见证人都可以给案例呈报人自己的反馈。
5. 提问和澄清
往往在言语呈报后,就会有提问的欲望。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对可能传声的情感反应的防御,或是该案例中分裂的情感的有可能呈现的重演。如果好些小组成员都以向案例呈报人提问的方式开始讨论,他们有可能镜像了来访者的心理动力(一种相似反移情)。因此,小组有自身的理解来访者阻抗和移情的方式(正如Kathryn的案例显示的那样)。除此之外,案例呈报中的遗漏部分指向了被督导人的盲点。我们问到“什么没有被呈报出来?”像“父亲如何呢?”“她的恋情与性生活呢?”这样的问题也会被提出来,并表明一些内在表征被压抑了,仍然停留在潜意识里(如Kathryn的案例中遗漏了童年创伤等信息)。
6. 反移情分析
这里对反移情的分析基于Oberhoff概括的步骤与层次。本文后部还会深入讨论对反移情进行分析的价值和意义。
Oberhoff建议了涉及反移情情绪反应的三个步骤:共情层面上的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情境层面上的理解(scenic understanding)、个人经历层面上的理解(biographic understanding)。理解过程的每一步或每一领域都要修通三个层次:注意及说出(noticing and naming);联想(associating);分析(analysing)。
共情层面上的理解指的是情感卷入,与Stern(1985)所说的“情感上的调频共振”相关,指小组成员和督导师与所呈报的素材产生共鸣。尔后,他们会反复进行短暂的认同、认知指称所感知到的(比如,体验到被抱持和被容纳的需要,并把这一感觉反馈给案例呈报人)。在联想时,被抱持的意象可能会浮现,比如,出现来访者与被督导人更亲近亲密的具体愿望。接下来的分析可能会揭示口欲期的需求,和/或来访者的部分退行,以及提供一个滋养的治疗关系的必要性。
情境层面上的理解需要来访者对治疗师重演早期冲突和创伤,想弄清到底是哪个内在客体被移情了(如,一个严苛的母亲,或情感上缺席的父亲);在这个情境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气氛。此处,联想的过程产生了社会角色的意象或童话故事的角色(如,巫婆,恶毒的继母,善良的仙女等等)。这样的分析可能可以一点点呈现和澄清来访者的内在客体关系。
个人经历层面上的理解探究的是反移情反应揭示的与被督导人相关联、或相冲突的个人素材。在一个督导小组中,这仅需要停留在“注意并说出”的程度,除非成员之间已经非常熟悉并建立的很深的信任。督导师应该保护被督导人,如有深入进行分析的必要,需要进入个体督导或个人治疗。在探索反移情议题的这一阶段,督导师会做出一些解释,将小组的镜像过程与来访者-治疗师互动的动力联系起来。
7. 建议和结论
最后,小组会就治疗过程以及下一步的干预产生一些观点和建议。同样地,这一过程有时候也以动作的方式出现,因为身体是信息的源泉,动作是干预的工具。作者,作为督导师,认为动态中的身体是发生改变的催化剂,尤其对被督导人专业上的自体而言。督导师需要确定,这些观点和建议对被督导者是否合适。最后,案例呈报人总结他/她的领悟,并检核最初的疑问和困惑是否得到了回答。
督导过程中移情与反移情分析的意义
你可以不停地分析来分析而无功而返。产生疗愈的是关系。
(Fairbairn, in Guntrip, 1975, p.145)
这一引用表明了在理解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上的根本转变。分析师不再是一个中立、被动、不参与的镜子的形象,而是在一个不断演进过程中的积极的参与者(Bernstein and Singer, 1982, p.3).
巴林特拥护客体关系理论,倡导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医学思想。Kohut(1977),Guntrip(1975)和Kernberg(1975)关注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客体关系的早期阶段。这是在Mahler et al.(1975)提出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认为个体最初由与他人的早期体验和经历所决定。该理论探讨个体需求的发展及在这些需求在外部现实中的被满足或受挫。
现今,Stern(1985)关于婴儿个体间世界的观念提供了一个深厚的发展模型。尤其是对舞动治疗师来说,Stern的观点结合了早期肢体和官能体验,以及与重要他人在节奏上的调频共振。客体关系理论及其在舞动治疗上的应用在此不作深入探讨,本段的重点在于探讨移情与反移情方面的不同观点,以阐明“镜像现象”这一分析性督导的核心概念。
“反移情”这个概念首先被弗洛伊德(1910)定义为针对病人的移情的对等的感觉。他认为,这些反应源自于精神分析师未解决的神经症性的冲突,是需要解除和克服的。此后,Heimann(1950)和racher(1968)强调了反移情反应在治疗上的正面价值和意义。Racher(1968)在治疗师的情绪反应上区分出三种反移情:神经症性的、一致的和互补的反移情反应。
l 神经症性的反移情是指治疗师在与来访者关联时,认同了自身婴幼儿时期的感觉。这是需要治疗师通过个人分析和治疗修通的。
l 一致性的反移情产生于分析师认同病人的自我。这样的反应产生于共情的过程,其特点是沉静和平稳的。
l 互补性的反移情产生于分析师认同于病人的内部客体。这样的反应产生于互动关系及投射与内射的动力,分析师被病人当做自己的一个内部客体,其特点是更困扰、激烈,甚至是不太舒服的(Fiedler, 1988,p.43).
作者强调在督导过程中,对一致性和互补性反移情反应的理解是分析来访者-治疗师关系必不可少的。在对舞动治疗师的督导中,Bernstein(1984,p.321)增加了身体和动作的维度,首创了“心身反移情”这一术语,指称治疗情境中的肢体和动觉感知。
反移情可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治疗师共享了个案无法言说的身体体验,或互补的,即治疗师经验到复杂情境的对立面,如,如果病人感觉正在遭受侵害,治疗师可能产生有如强奸犯的心身想象。
(Bernstein, 1984, p.328)
这就谈及了治疗师内在体验的一个全新的维度。对动觉的感知是舞动治疗师有可能吸收和代谢来访者分化的部分,和自己身体的投射、移情反应。
在巴林特小组的督导过程中,以及在对舞动治疗师的精神分析取向的督导中,正是在分析这种涉及移情和反移情议题的来访者-治疗师关系的心理动力。督导中,反移情反应在以下三种关系形式中发生(Balint, 1966, p.410),这是督导师需要牢记以聚焦在个案工作上的:
1. 来访者-治疗师关系(关于该案例的)
2. 被督导者-督导师关系(关于被督导者的)
3. 被督导者-其他小组成员的关系(关于督导小组的)。
1. 来访者-治疗师关系
对舞动治疗师的督导特别关注案例工作本身。案例呈报过程中,小组成员试着去体会和觉察被唤起了什么感觉。巴林特发觉小组成员与团队进程与该案例的情感面向及心理动力有关。
小组中有这样一个趋势:呈报案例的医生表现得像病人,而小组表现得像医生。咨询室里的情景因此很戏剧性地在小组中重现。
(Balint, 1966,p.401)
这被称为“平行进程”。Searles(1961)称之为督导晤谈中的“映射”。在德国,Argelander(1973)和Loch(1989)倾向于使用“镜像现象”这一术语,来说明来访者-治疗师关系,来访者的主要冲突,阻抗和/或潜意识移情的议题大多在小组成员和小组情境中重现,并被镜像了。为区分初始情境(在治疗晤谈)和镜像情境(在督导小组中),Dantlgraber(1977)建议将它们看成是第一、第二次序上的移情-反移情的动力结构。
2. 被督导者-督导师关系
在被督导者与督导师之间的移情与反移情的议题与父母和权威议题有关,逐渐显露出不同阶段上的理想化,服从,反叛,同化和自我确认。被看见和被支持的需求,被允许分离和与众不同的需求,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的愿望也被表达出来。这些议题需要被分析,尤其在对实习期间的对照分析进行个体督导时。在督导小组中,作者较少分析被督导人在这一层面上的移情议题。如果这是神经症性的,被督导者将在个体督导和个人体验中得到支持来修通。
在大部分的案例中,督导师也是案例中权威冲突的表征。这就需要被澄清和意识到,目的是理解在来访者和治疗师关系中父母角色的意义和移情。如果督导师对此没有恰当的理解和分析,被督导人可能会与来访者重演其未解决的议题,这就是“对等镜像现象”,如,对督导师不加分析的理想化可能让被督导人/治疗师也期待来自其来访者的理想化。
3. 被督导者-其他小组成员的关系
第三个层次,被督导者(即案例呈报人)和小组的反移情反应,被放置在所呈案例中来探讨。有时,小组的反应犹犹豫豫地,或感觉无聊,或对案例呈报人大加批判。这时,督导师需要点明这种动力,并始终聚焦在案例上,利用这些情感反应来分析所呈案例的动力,而不是将重点转移到直接去体会、处理这些感受。
督导小组及成员的发展性进程
一个新的督导小组开始时总是会有矛盾心理。成员们期待改变,同时又感知到对改变的恐惧。德文谚语“洗涤我吧,但别把我弄湿了”恰能形容这种矛盾心理。参加督导能让人意识到自己职业角色和定位的局限性,也可能为治疗性自体带来改变和成长。对一些成员来说,探索自己的局限性一开始会显得危险,可能会因为不够好、了解得不够多而感到尴尬或羞愧。督导师需要打造一个可以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的氛围。巴林特(1966,p.407)称之为“面对自己的愚蠢的勇气”。
督导师需要密切注意小组进程的节奏和发展性的动力。Schutz(1958,p.58)发展出四阶段的团体动力概念。这一概念探讨了小组中的个体对应各个发展阶段的相关的情感主题:
1. 融入:矛盾,好奇,开放,不安全,想去相信,消极,调整(在新的督导小组的头几次见面中)。
2. 控制:力量争夺,攻击,个体化,分离,活动,后撤,坚持己见(接下来的几次见面中明显地呈现这些主题)。
3. 情感:责任,安全,成效,支持(贯穿在此后的进程中)。
4. 分离:哀痛,愤怒,避免悲伤,反馈,总结,放手(督导小组的结束期)。
作者观察了舞动治疗师小组在督导过程里历经了这些阶段。除此之外,每一个成员还通过对督导师和其他小组成员的理想化,反叛,后撤和坚持己见处理着他们自身职业胜任力的内在议题。在晤谈中,了解和记住这些团体的方方面面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会与实际的案例工作重叠,或形成干扰。这些需要被点出来,和进行解释,这是为了案例的讨论,而非为了自我体验和治疗。
小组领导者的角色
巴林特坚信,巴林特团体的技术中最重要的方面是领导者对于带领小组的态度(Balint, 1966, p.409)。她/他不用将自己看做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无所不知的专家”。“小组领导者”的角色的特征是友好,对成员的专业工作的好奇。以自由流动的注意力的方式来倾听对小组的氛围来说是十分重要的(Balint, 1966, p.403)。为了小组进程的发展,她/他需要耐心和克制。她/他汇集各样的观点,并给出进行解释的思路。另一方面,她/他应该也视自己为跟大家平等的小组成员,愿意向其他成员学习。她/他会犯错,不完美,并允许(可能甚至邀请)批评和异议,由此也为小组成员树立了不因批评而尴尬或羞愧的榜样。Beucke-Galm(2001, p.23)列举了督导师进行支持性对话所需要的能力:
暂停(suspending):让思考、评估暂停;
倾听(listening):保持非偏见,空杯和开放的态度;
表达(voicing):说出内在的感知,意象和动觉反应;
尊重(respecting):尊重和认可他人本来的样子。
巴林特模式的局限
对巴林特模式的最大批评是缺乏对机构设置的思考。这是因为事实上巴林特工作过的全科医生们多为私人执业,并不在大型机构里工作,因此不需要考虑从任何其他失调的情况。当治疗是设置在一个大型机构中的(诊所,复健中心或精神病院),为了充分地理解各种动力,除了思考来访者-治疗师关系之外,还应考虑设置中的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巴林特模式仅仅探讨个体能力来处理情境中的失调结构,而没有分析情境本身。
在此,Rappe-Giesecke(2003)的整合取向为机构内的协作带来了更多的思路和视角。舞动治疗师的角色定位,团队的期待,以及机构中的等级结构都需要被分析。多数情况下,来访者被主管医师转介给舞动治疗师;有时,治疗目标由个案的心理治疗师来决定,舞动治疗师们感到无助和无力。挫败沮丧感或无所不能感(应对无助感的防御)交织在一起,会干扰到来访者-治疗师的关系。因此,需要首先理解和督导这些冲突,然后,个案工作才能继续。通常,这些冲突潜藏在案例呈报中,停留在潜意识层面,除非督导师将之提出来。督导师必须将团队中的投射和移情的议题,团队结构,和机构的结构等结合起来。这样,督导师才能跨越巴林特小组的局限性,在特定的机构和设置中更充分地支持舞动治疗师。
总结
本章讨论了巴林特小组模式督导舞动治疗师的优势及局限。如果督导能结合身体层面动作表征的动觉方式,真实动作和见证,以及心身反移情的概念,就能将言语和动作中联结起来。由此,舞动治疗师可以经验到对自己专业自体的反思,而且是在一个考虑整个客体关系的更令人满意的水平上。此时,督导师所创造了更多的内在自由,尤其是在与来访者关系上做出选择的自由。
除此以外,本文还阐明督导师越多地考虑机构运转不良的情境,督导过程就越具有支持性。尽管督导的直接目标并不在与个人体验和治疗,在对职业行为进行的反思中仍会收获不同程度的个人成长,和专业上的独立性。
References
Argelander, H.(1973) Balint-Gruppenarneit mit Seelsorgern. Psyche,27,pp.129-139. Balint, M. (1957) The Doctor, his Patient and the Illness. London: Pitman Medical.
---(1966) Der Arzt, sein Patient und die Krankeheit. Stuttgart: Klett-cotta.
Bender, S (1990 )Ein gruppentherapeutischer Ansatz in der Tanztherapie. Jahrbuch Tanzforschung Bd. 1, Wilhelshaven: Florian Noetzel verlag, pp.59-81.
Tanzforschung Bd.1, Wihelshaven: Florian Noetzel Verlag, pp.59-81.
Bernstein, P.L.(ed.)(1984)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Dance-movement Therapy, Vol.II. Dubuque, IA: Kendall/Hunt.
Bernstein, P.L. And Singer, D.L.(eds)(1982) The Choreography of Object Relations.
Antioch/New England: Graduate School, Keene, NH.
Beucke-Galm, M. (2001) Dialog in der lernenden Organisation. Zeitschrift fuerOrganisations-entwicklung, 1, pp.20-31.
Brandau, H. (ed.)(1991) Supervision aus systemischer Sicht. Salzburg: Otto Mueller. Chodorow, J. (1986) The body as a symbol: dance movement in analysis. In N. Schwartz-Salant and M. Stein (eds) The Body in Analysis. Wilmette, 1L: Chiron, pp.87-108.
Dantlgraber, J.(1977) Ueber einen Ansatz zur Untersuchung von 'Balint-Gruppen'.Psychosomatic Medizin, 7, pp.255-276
Dosamantes-Alperson, E.(1984) Experiential movement psychotherapy. In P.L. Bernstein (e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Dance-movement Therapy, Vol.II. Dubuque, IA:Kendall/Hunt, pp.257-291.
---(1987)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issues in movement psychotherapy.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14,pp.209-214.
Fatzer, G. And Eck, C.D. (eds)(1900) Supervision und Beratung. Ein Handbuch. Cologne: Agentur Himmels.
Fiedler, I. (1988) The Interdependence of Kinesthetic Empathy and Somatic Counter-transference in Dance/Movement Therapy.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Foulkes, S.h.(1974) Gruppenanalytische Psychotherapie. Muenchen: Kindler.
Freud,S. (1910)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Psychoanalytic Therapy. Standard Edition,Vol.11, pp. 139-152.
---(1992)Vorlesungen zur Einfue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Vienna: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csher Verlag.
Guntrip, H.(1975) My experience of analysis with Fairbairn and Winnicot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2, pp.145-156.
Heimann, P. (1950) O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1,pp.81-84.
Jacoby, M.(1984) The Analytic Encounter. Transference and Human Relationship. Toronto: Inner City Books.
Kernberg, O.(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Jacob Aronson.
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Lippenmeier, N.(1984) Beitraege zur Supervision. Kassel: Public des Fachbereich 04 Gesamthochschule Kassel.
Loch, W.(1989) Balint Seminare: Zweck, Methode Zielsetzung und Auswirkungen auf die Praxis. In c. Nedelmann and H. Ferstl (eds) Die Methode der balint-Gruppe. Stuttgart: Klett-cotta,pp.217-236
Mahler, M, Pine, F. And Bergmann, A. (1975) 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the Human Infant. New York: Basic Books.
Oberhoof, B.(2000) Uebertragung und Gegenuebertragung in der Supervision. Munster: Daedalus.
---and Beumer, U.(eds)(2001) Theorie und Praxis psychoanalytischer Supervision. Munster:Votum.
Pallasch, W. et al. (eds) (1992) Beratung, Training, Supervision. Weinheim/Munich: Juventa.
Puhl, H. (ed.) (1990) Handbuch der Supervision-- Beratung und Reflexion in Ausbildung, Beruf und Organisation. Berlin: Edition Marhold.
Racker, H. (1968)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Rappe-Giesecke, K.(2003) Supervision fur Gruppen und Teams. Berlin: Springer.
Samuels. S.(1985) Countertransference, the 'Mundus Imaginalis' and a reserach project.Journal of Analytic Psychology, 30,pp.47-71.
Schreyogg, A.(1991) Supervision- ein integratives Modell. Paderborn: Jungfermann.
Schutz, W. (1958) A Three-dimensional Thero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New York: Rinhart.
Searles, H.F. (1962) Problems of supervision. Science and Psychoanalysis, 5,pp. 197-215.
---(1979) Countertransference and Related Subjects. New York: Ine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Siegel, E. (1982) Object relations and the psychoanalytic supervison of dance-movement therapist. In P.L. Bernstein and D.L. Singer(eds) The Choreography of Object Relations. Antioch/New England: Graduate School, Keene, NH, pp,167-193.
---(1984) Dance-movement Therapy: Mirror of Ourselves. New York: Human Science Press.
Stern, D.N.(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New York: Basic Books.
文章来自 北京阿波罗教育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