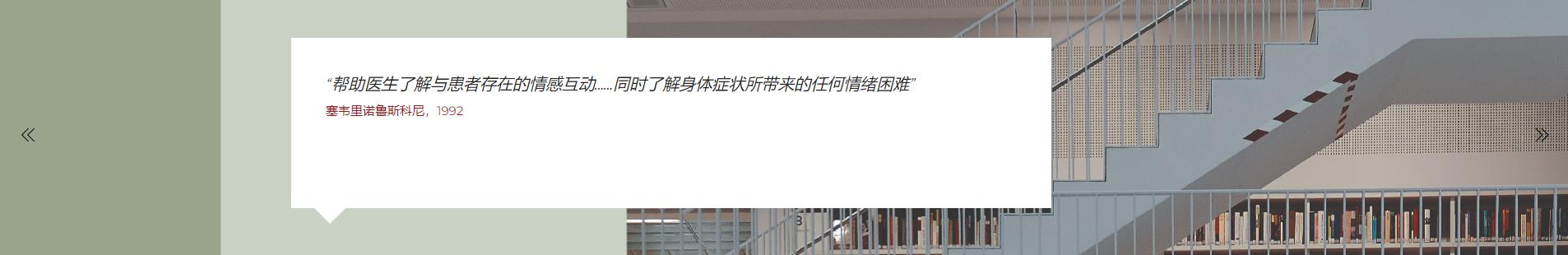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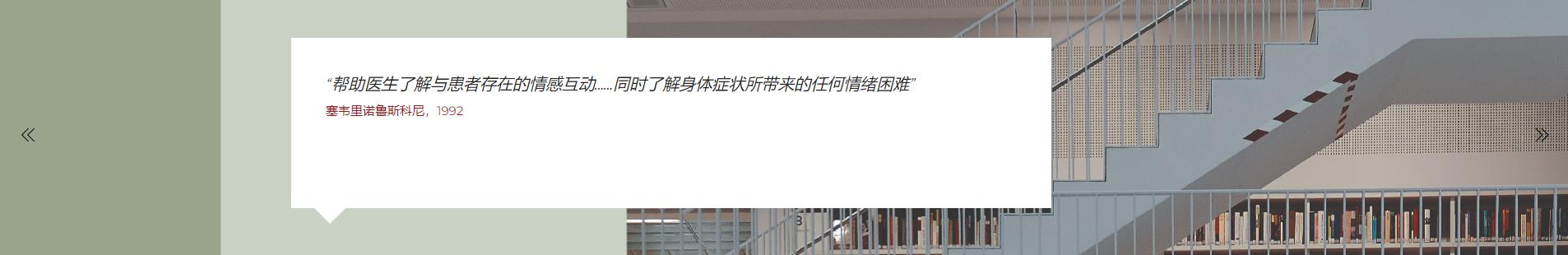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9月21日下午,年会分七个学术分论坛进行小组分享和讨论。小编参与了“社区心理技术与应用”板块的分论坛,获取了各高校老师、同学所做课题研究的一手资讯。现在将其中一个课题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它的主题为:巴林特小组及其在社区柔性治理中的应用,由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的刘佳怡、凌辉、张建人、彭松黎和甘义共同完成。
一.什么是巴林特小组
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是匈牙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和社会工作者伊妮德·阿布(Enid Albu)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伦敦所创建的。最初旨在“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模式指导下,训练全科医生处理医患关系。
巴林特小组是指,在安全、隐私、尊重的环境中,通过案例报告、清明模拟、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的“案例再现”,使案例报告者有机会重新描述自己经历过的医患冲突,并在此体验这些印象深刻、无法释怀或让人感到棘手、无助、愤怒、沮丧、挫败等困扰已久的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的情景所带来的的感受,然后通过小组讨论,借助移情与反移情、自由联想和投射认同等技术,帮助案例报告者发现自己忽视的重要细节,认识到在单个视角中特定的“盲点”,形成新的视角与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实现关系的良好互动(Horder,2001;赵建平,2012;巴林特,2012)
二.巴林特小组的特点
(一)小组活动过程提供了“金鱼缸”的全景式视野。
活动大致流程为:几个人组成小组,由案例报告者陈述,之后退出小组,由其他几人共同围绕案例讨论。此时报告者能够站在上帝视角,来审视自己之外的这个场域,故叫做“金鱼缸”式的全景视野。期间也可引入“雕塑”技术,更加促进其观察到此前忽视的人或事。
每个人都像一面镜子,给他人找出他自己平时看不到的、被忽略的东西。通过小组讨论,个人的感受各不相同,收获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二)整个活动过程中,体现着“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组员各自自由分享自己的感受与想法,相互讨论,组员需遵守保密原则,保持尊重,不评判,不给予解决方案与建议,自由讨论,没有正确与否的答案,各种关系的动态被直观地展示出来。指导者需经过严格专业培训。
(三)巴林特小组基于的理论前提是:人不仅对药物有反应,对医生也有所反应。也就是医患关系本身就具有治疗作用,通过在小组当中的叙事和全景观察。
(四)最终目标不是为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提出、接受建议,而是从关系的不断变动角度,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关系建立中的困难,从而形成新的理解,帮助小组成员成长,提高其与病人的互动沟通能力。
(五)近年来,巴林特小组被推广到各种领域各种群体中使用。
例如,临床医疗工作、医疗教育、高校教育和社会工作等领域,心理学家、教师、护士、婚姻家庭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助人的职业人群。
(六)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使得巴菲特小组不仅适用于医患关系,也适用于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同伴关系、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等人际关系中,但要注意小组活动的成员都属于同样的角色身份。例如,在改善亲子关系的小组中,家长可以组成小组,而避免孩子加入。
三.巴林特小组是如何起到作用的
(一) 小组用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得困难案例中的情绪得以表达。
(二)帮助案例提供者度案例形成新的、不同的理解。
(三)发现我们在医患关系中的盲点和潜在假设。
(四)帮助小组成员减少在困难案例中挣扎时所体验到的孤独与羞愧,并对新的学习有开放态度。
(五)帮助小组成员成长,并且发展作为医院与其患者相处的能力。
四.巴林特小组的主要价值及意义
(一)缓解负性情绪,提高情绪智力;
(二)改善沟通模式,提升人际交往能力;
(三)提高共情能力
(四) 降低职业倦怠
五.为什么要进行社区柔性治理
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和基石,其治理的好坏往往决定了整个城市的发展,继而影响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曹海军,2018)。”
“社区”“社会治理”等概念正式成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我国学者也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发现,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硬治理的弊端日益显露,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不高,缺乏自治主体性,从而使社区治理陷入困境之中。以往合计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不能有效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的诸多新问题。在政治压力型体制下,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容易导致社会失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很有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周根才,2014;于建嵘,2009)。
政府愈加认识到社区治理需从“刚性治理”向体现人文关怀的“柔性治理”转换,从而激发社区内部自治动力与活力。
六.巴林特小组与社区柔性治理的契合点
两者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理念。
社区治理的主体是人,包括个体及其代表的组织。无论是社区建设,还是社区治理或管理,都应该把“人”作为核心。个体的治理能力、组织的治理效能决定了社会治理的质量(辛自强,2018)。
目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缺乏一定的人本精神,忽视了个体的主体性。社区治理主体仍处于“忙于行政事务,却无法获得成就感”的困境中,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不高,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倦怠感日趋增强,社区工作者与居民双方因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容易产生冲突(楼烨,郑振佺,2011)。
有学者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对治理技术(主要是调整人际关系的组织管理技术)学习与运用的忽视(陈伟东,吴恒同,2015).
巴林特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致力于心身医学思想的传递。他利用小组讨论的形式,将精神分析中的“人文关怀”带到了日常的医患关系之中,让医生更多地关注病人心理,而不仅仅只是机械地诊断和开处方。
这种思想与理念也是迫切需要用于其余领域的,就像医生不能只关注病人疾病,教师不能只关注学生成绩一样,社区治理中需要这样“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方式,从而激发社区内部自治动力与活力。
七.巴林特小组能够有效解决社区治理困境
研究表明:巴林特小组聚焦于双方关系的互动,能够缓解负性情绪、改善沟通模式、提高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缓解职业倦怠。巴林特的客体关系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其在心理治疗和婚姻问题等领域的发展。
巴林特小组的共同创始人伊妮德是注册临床社工,巴林特小组的假设和基本理论中也蕴含了社会工作的基本思想,所以将其运用于社区治理当中也是合适的,也将成为该工作模式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巴林特小组应用于社区治理中,能为社区居民解决他们所迫切关注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构建社区幸福小家;帮助社区管理者更好地理解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对自身人格产生“细微但显著的变化”,提高其治理能力,获得自身职业支持与发展,构建良好的社区组织体系;帮助家校社处理好三方联动关系,师生关系以及各主体的同伴关系或人际关系,从而实现社区和谐发展,达到“柔性稳定”的健康状态。
本次研究重新审视巴林特小组与社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家校社联动关系、社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等人际关系的应用与实践上贡献了新思路,为推动巴林特小组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构建和谐社区提供了新方法。
文章转载自:百目信真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