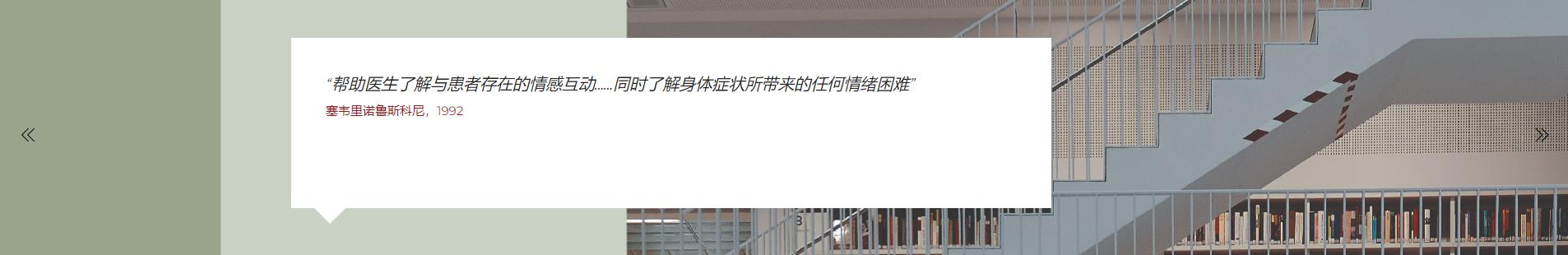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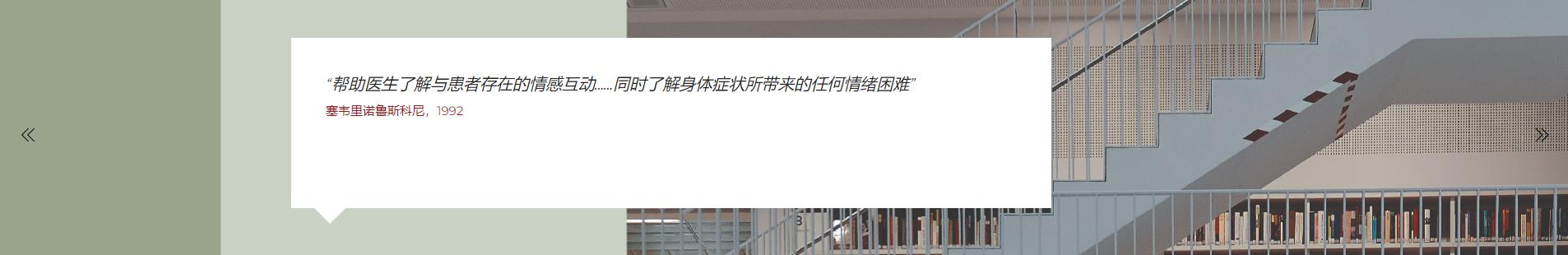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我厌倦了这份工作,厌倦了这些无聊和抱怨的病人。
我走进诊所希望尽快离开。
当病人开始说太多话时,我会站起来轻轻地指出其他人在等待。
赶紧赶到诊所的关门时间,实在是太着急了…… 还记得我几年前告诉过你吗?他们是一群在医患关系中训练的家庭医生,对与患者的关系感兴趣,从关系的角度呈现临床疑难病例,并在他们之间进行讨论。我有一个好朋友,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小组的领导者,给他打电话,我会给你电话号码,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
经过几个月的重新思考,我决定,打电话并参加了萨龙诺的“巴林特”小组的一个晚上。
由于这次经历,我极大地重新评估了家庭医生的形象,我发现在不提供解决方案、处方或药物的情况下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患者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从未评估过简单倾听的这一特殊方面:我从大学开始就习惯于解决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我无法找到患者要求的解决方案,我会感到紧张,因为通常没有解决方案:我希望每个人都承担费用找到答案或解决他们的问题:无法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怒,我不可避免地会对下一个病人出院。
我发现了让他们抱怨的重要性。
现在我喜欢听他们说话,让他们发泄,给他们时间……他们变得更友善了,他们不时问我:“你是医生,你好吗?”
他们也对我感兴趣。多么棒的感觉!

和克拉拉在一起这些年,十五岁多,听我说话是自发而轻松的,不假思索:一个好女人,充满活力,兴趣盎然,她是一名演员,旅行,穿着五颜六色的连衣裙和围巾,她多动。她总是面带微笑,带着一些小病进了诊所,接受了检查,听了我的意见,很用心地听我的话,然后几乎掩饰自己打扰了我,总是很高兴地出去。
十年前,她患上了乳腺癌,通常的手术是:手术、化疗、放疗、六个月一次的肿瘤检查。
疾病吓坏了她,造成了一些焦虑和恐惧,但她的反应是积极的,她一如既往地战斗,以她一贯的求生意志;治疗的结果让她感到不安,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数字,其中一个
许多人觉得她没有被肿瘤学家视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名遵守协议的患者。
化疗后他又开始旅行,演一些节目,看书,他还告诉我一段新恋情。
有时她带着一些小病在工作室来找我,因为害怕复发而焦虑不安:她希望得到保证,她所指责的痛苦与她的疾病无关。但他说话和行为的方式让我没有感觉到他的焦虑投向了我,他也没有寻找不可能的答案,他向我传达了他的恐惧,但同时他告诉我他最后一次感受到的情绪旅行或他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我听了她的话,有时我给她开了抗焦虑药,但最重要的是我听了她的话:我喜欢听她的话。她告诉我,她从我身上走出来的时候更加平静和安详。我总是对他的话感到惊讶,毕竟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做太多事情。有时她在旅途中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的一些小病:我听她的,我试图为她的症状找到一个解释,她平静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焦虑,但受到控制,几乎是抱歉,同时又具有讽刺意味。
大约两年前复发:先是纵隔,然后是肺和脑。一开始,肿瘤学家对治疗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得到了她和我的认可:有必要尝试一切并进行斗争。
克拉拉能够在一次化疗和下一次化疗之间采取行动和旅行:她的生存意愿和热情赋予了她非凡的力量。她的头发掉了,但她没有戴假发,而是戴了一条五颜六色的围巾,总是和她的裙子颜色相配。
几个月后,治疗狂怒对我来说不再是合理的,疾病太严重了,非常虚弱,治疗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是毁灭性的。克拉拉也开始怀疑他们的结果:她还抱怨肿瘤科医生变得回避,在访问期间他们总是很匆忙,没有人说超出必要的内容,他们避免回答她的问题。
我也开始陷入困境:我去了她家,我拜访了她,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很尴尬。有一天,除了常规的化疗外,肿瘤科医生还为她提供了一次家庭姑息治疗的专家访问(在我看来,是为了摆脱它,而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当他告诉我时,我觉得我的脚下好像没有了大地:就像被判了死刑。
它本能地出来了,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什么姑息治疗!现在最好的事情是她和我要吃披萨”。她亮了起来,她很高兴,几乎不敢相信。他立即接受并问我是否可以互相交谈。
当我意识到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东西时,我很害怕:我告诉了她什么,什么晚上在等我,此时我该怎么办,我们会谈什么?
幸运的是,周三有“Balint”,我能够提起诉讼并与我的同事分享我所做的“麻烦”。
我承认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给巴林特打了一个案子之后,在听了别人对我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之后,我总是松了口气,很满意,我更清楚我之间发生了什么和病人,那一刻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为什么我会紧张或感动,我更清楚我必须做什么以及我可能在哪里犯了错误,但我很难谈论发生了什么在群里说,总结一下各种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
在我将克拉拉的案子带到“巴林特”的那个晚上之后,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对她和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得不继续追随我的直觉,就像我一直对她做的那样。
这些天我不得不尝试简化并像往常一样听它。
比萨店的晚上非常愉快:克拉拉穿着紫色的裤子,一件色彩鲜艳的夹克和一条与裤子同色的围巾:她走路很困难,她化着妆,微笑着。那是九月,天气还很热,我们去了她家附近有花园的比萨店:我们半小时走了大约 100 米,她累了。
晚餐时,她告诉我她作为演员的生活片段,她多年来没有家,只有一个大箱子跟着她,关于最新的爱情故事,关于她正在读的书:我听她觉得好笑。反过来,我向她讲述了我的生活片段,但难度很大,好像我想给她留出更多的空间。
他告诉我,除了探访或治疗外,他已经有一年没有离开过家了。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他的病。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他的一些邻居,他们很惊讶地看到我们在一起,他们邀请我们喝一杯酒,为我们的夜晚干杯。
在 2 个月内情况恶化:他抱怨严重的呼吸困难和疼痛,我害怕无法用我的疼痛治疗技能来控制。
我们决定共同启动姑息治疗。
克拉拉总是向我提交姑息治疗医生的报告,如果我不同意,她什么也不做。我定期去她家,她告诉我困难,与仍然为她提供新疗法但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的肿瘤科医生的争吵,她的朋友和害怕和她睡觉的伴侣的来访,我听着,我在听...
最重要的是,她抱怨没有人告诉她事情的真相:肿瘤学家掩盖了她的问题,他们总是很着急,他们没有做出预测。我听了她的话,但她没有直接问我问题。
参观完它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在我看来,我只剩下不到十五天了,你怎么看?
“我没有水晶球,但我认为你是对的”我微笑着回答,奇怪的是并不尴尬。
他冲我笑了笑,谢谢我。她告诉我,那天晚上她想和她的朋友们在她家组织一次晚餐。
我告诉她我想拥有她自己的书,一本她读过并喜欢的书。
他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考虑一下,然后给我。
我离开了他的房子,我并不难过,我很好,我想走路,深呼吸,在树丛中。
第二天下午,克拉拉死了。
她没有时间为我选书,但在与朋友共进晚餐的晚上,她告诉洛伦扎她应该给我一本她的书,她想考虑一下。
几天后,洛伦萨来到工作室,给我带来了克拉拉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匹克威克圈》:一本活生生的书,有“厚”的书页,上面覆盖着彩色纸,颜色和她的衣服一样.
文章来自:意大利医学协会巴林特项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