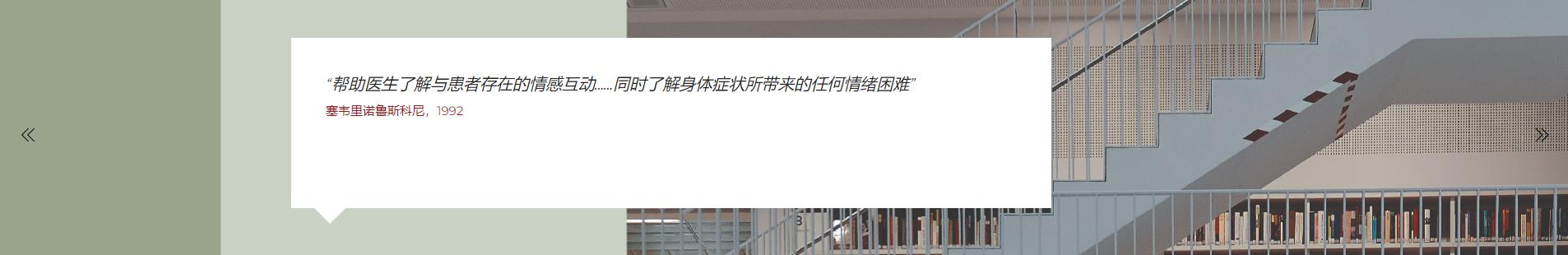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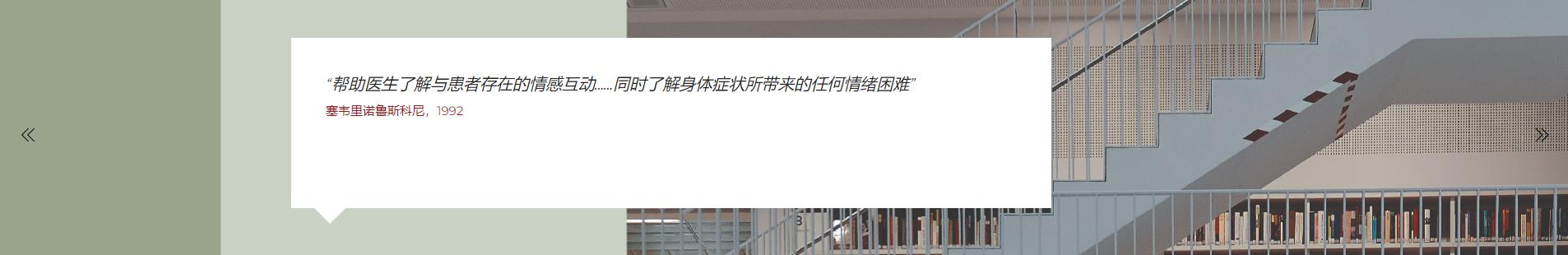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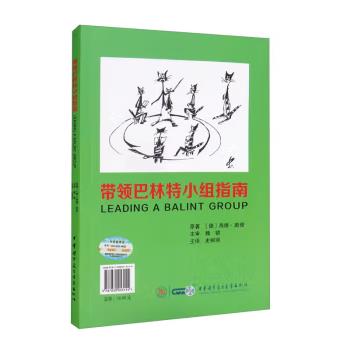
书籍目录
01 米歇尔·巴林特是谁
02 巴林特小组是什么
“经典”巴林特小组
有附加元素的巴林特小组
“金鱼缸”小组
组长研讨会
案例讨论小组
治疗团体
督导
03 巴林特小组不是什么
自我体验团体
04 巴林特小组的组长要做什么
伦理假设与限制
案例提供者和组员的安全性
保密原则
解决冲突
怎样处理攻击性
05 副组长要做什么
支持组长
反映小组进程
照顾组员
06 平行进程
参加组长培训的要求
阶段和标准
07 组长的培训
经典的巴林特小组
带有其他元素的巴林特小组
在经典巴林特小组中
08 巴林特小组组长必须意识到什么
在有雕塑的巴林特小组中
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小组
09 带领不同的小组
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的小组
学生的小组
其他助人工作者的小组
不同文化背景和国籍
在结构化和放手之间,不同小组的不同风格
有主持人的督导小组
10 巴林特小组组长的督导
内视团体
11 组长的任务
通用任务
带模拟小组中的任务
组长遵守模拟的目的
组长意识到的副作用
12 结论
13 国际巴林特联盟——巴林特小组组长认证标准
14 德国的巴林特小组组长认证标准
临床医生必须满足的要求
心理学家必须满足的要求
15 参考文献